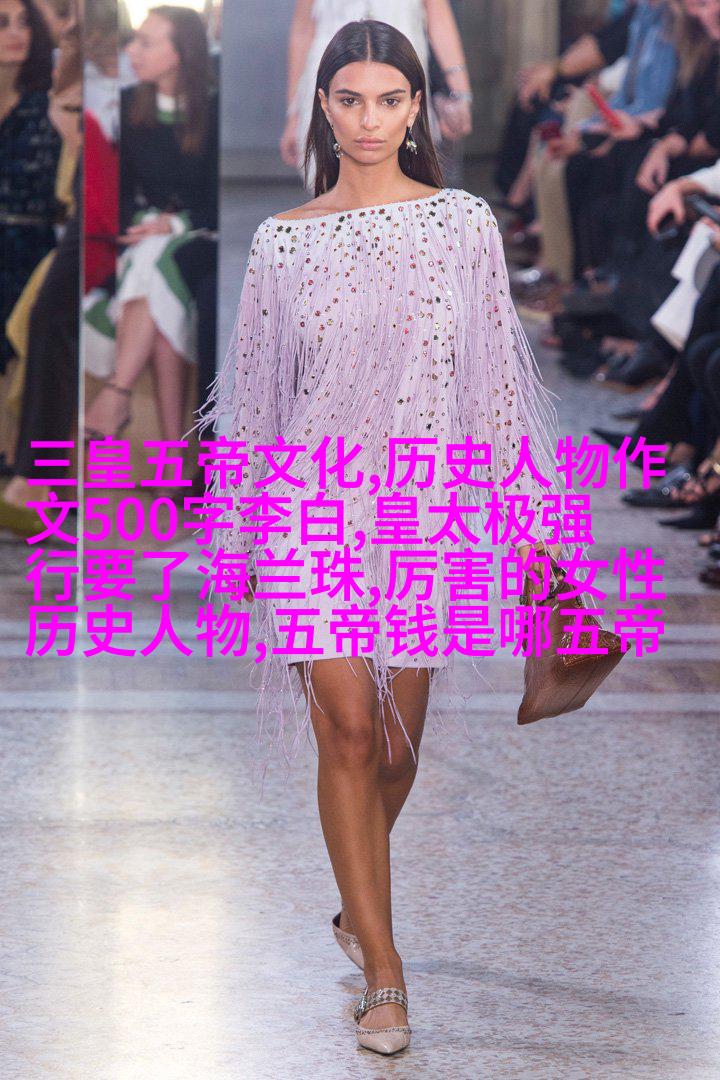郑大同,作为一位深受京剧文化影响的学者与票友,他在青少年时期就已对京剧产生了浓厚兴趣。记得他上中学时,便是一名小票友,曾有幸演出《贺后骂殿》中的经典段落“有贺后在金殿一声高骂”,台下的掌声如潮汹涌,令他几乎达到忘我的境界。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热情并未减弱,而是更加坚定。在大学时代,他常常用冷烧饼钱去观赏程先生的表演,即便学校散戏后大门紧闭,也不介意翻墙而入。1942年,他从哈佛大学拿到了硕士学位回到天津,就准备结婚,但当他得知程先生将在上海进行演出时,毅然放弃了去杭州蜜月之旅,与新娘子一起频繁地前往戏院中欣赏程派艺术。
程先生对于与大学生交往颇为倾心,对于郑大同也给予了特别关照。当时,一位朋友将郑拍摄的程先生剧照转交给了他,并听闻这位学生为了观看他的戏而放弃蜜月旅行的事迹,程先生被深深感动。他安排和郑见面,从此两人成为至交,每次相聚都能聊到凌晨,为彼此提供宝贵建议,使郑的大师级唱法不断进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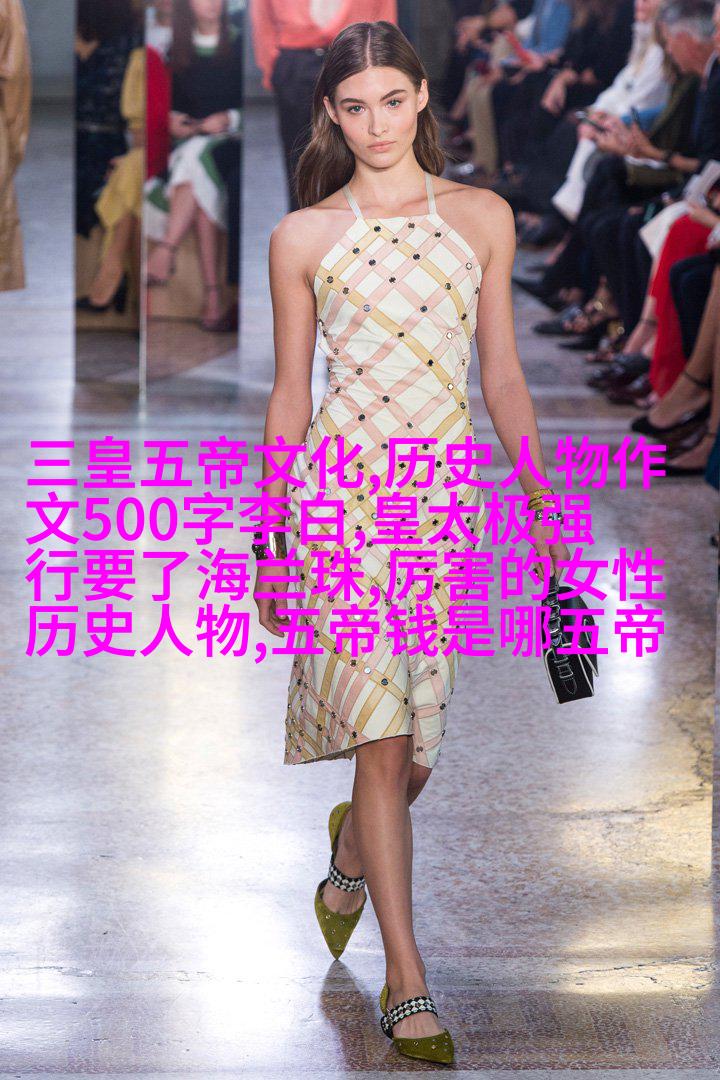
1945年,当钢丝录音机刚刚进入国内市场,价格昂贵之际,郑老师努力筹集资金购买了一台,用以收录程先生精彩绝伦的实况演出。1946年的9月份,在抗战胜利喜讯传来之际,程先生连续在上海进行36场独家本戏表演。郑老师全数记录下这些珍贵的声音,这些资料成为了保存和研究京剧宝库不可多得的人文财富。
1963年的8月,在江苏省青年京剧团上海巡回展出的盛况下,由于黄赤波公安局长介绍认识钟荣,这位青年才俊短短四个月内便学会了五部古典名段:《梅妃》、《文姬归汉》、《祝英台抗婚》、《贺后骂殿》以及《三击掌》,其勤奋刻苦令人钦佩。此外,还有其他许多优秀艺人,如新艳秋、赵荣琛、王吟秋、唐在炘等,每次来到上海,都会亲切拜访这位尊敬的大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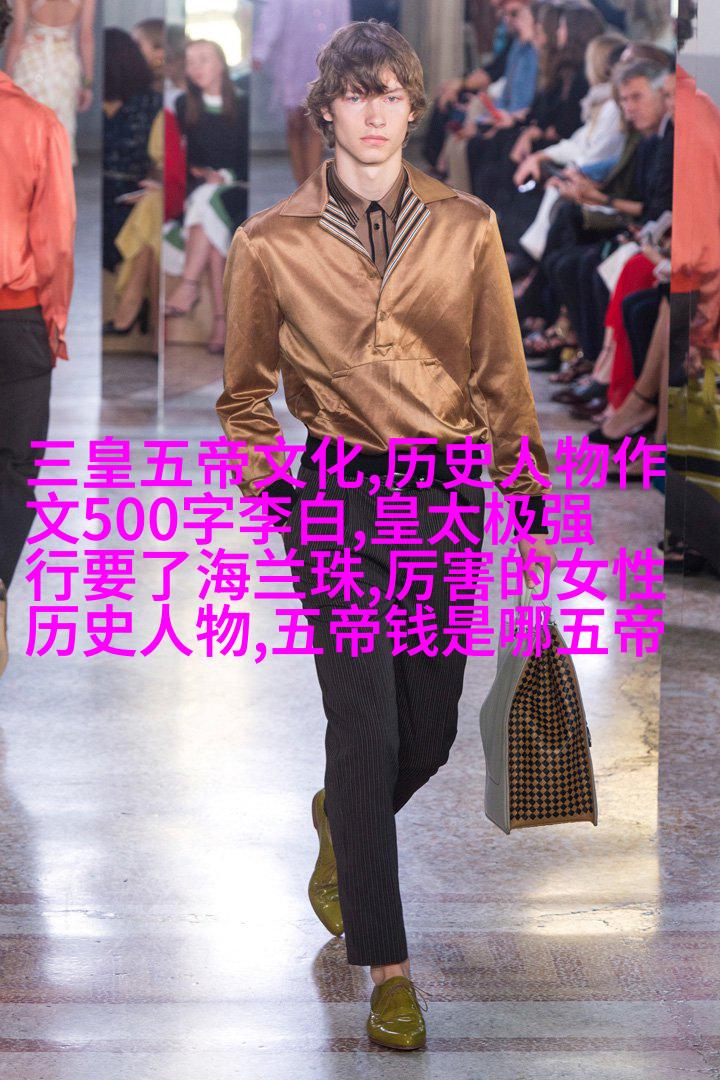
1953年,当节目结束后的26场《祝英台抗婚》的表演告一段落之后,无论是在唱腔还是身段上的细微变化都值得赞叹。这也是对艺术追求极致的一种体现——即使是相同的一部作品,每一次呈现都是新的挑战,不断提高,以满足观众日益增长的情感需求。而对于那些改变最明显的地方,如1929年的老唱片与1946年及1953年版《金锁记》的二黄散板歌词差异,更是展示了一种艺术品质上的超越性和丰富性,不仅没有所谓正宗或非正宗的问题,更反映出了一个艺术形式如何不断前行向前发展。
关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这样说:尽管历史变迁让一些美好的东西遭遇沉浮,但通过人们共同努力,它们依然能够延续下去。20世纪60年代初,当李玉茹老师因舞台上扮演梅妃而受到批评甚至迫害的时候,有人认为这是复古文化不合理地被打压的一个缩影。而十几年后的80年代初,当李玉茹再次希望恢复这一角色,她找到了指导她的人——那就是那个始终以诚待人的伟大的导师—— Zheng Da Tong 教授。他既教会她技巧,又教会她品德,让她的每一次舞蹈都充满了一种无私奉献的心态,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百花齐放春天精神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