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片宁静的自然之中,郑大同以一颗热爱京剧的心,对京剧脸谱颜色代表的深意进行了细致的探究。他的研究不仅融合了对自然美的领悟,也成为了他成为京剧票友中的学者型典范的一个重要标志。在那个年代,他作为一名小票友,在天津上中学时就已经被《贺后骂殿》的精彩表演深深吸引。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不仅是程先生的粉丝,更成为了一位亲密的朋友和学生。

程先生特别喜欢与大学生交往,这也让郑大同有机会结识这位京剧大师。他为程拍摄了许多剧照,并将这些照片送给了程先生。当程听说这位大学生为了看他的戏而放弃了蜜月旅行,他非常感动,便安排在化妆室与郑见面,从此二人便成了至交密友,每次见面都要聊到深夜,讨论唱腔和艺术。
1945年,当钢丝录音机刚刚在国内上市时,郑老师即刻购买了一台,用来收录程先生实况演出的珍贵音轨。这份宝贵资料,不仅记录下了1946年的36场连续演出,也成为了研究程派艺术的一本厚重教科书。在1963年,江苏省青年京剧团在上海演出时,公安局长黄赤波向钟荣推荐郑大同老师,这个四个月内钟荣学习《梅妃》、《文姬归汉》等五出戏,就如行云流水般顺畅无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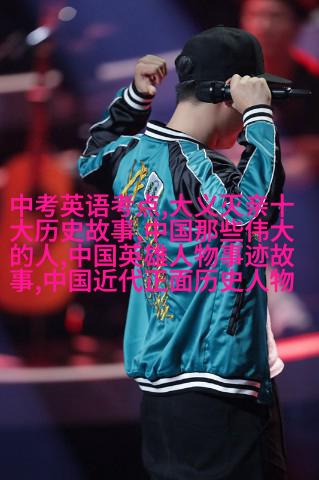
除了对唱法、曲调以及舞蹈技巧上的严谨分析外,郑大同还留心观察到了程序中的变化,无论是在早、中、晚三个不同时期,都能发现不同的风格和改进。他通过对比1929年的老唱片与1946年的现场录音,可以看出词和腔之间不断地发展和完善。
由于其诚挚待人以及卓越的人品魅力,使得郑大同赢得广泛的人缘。不管是在教育界还是票房界,只要提及他名字,都会有人口碑传颂。20世纪60年代初,他因教李玉茹一出《梅妃》,上演后震撼全城,但十年之后,《梅妃》却被批评为“复旧罪证”。尽管如此, Zheng Da Tong 仍然没有怨言,而是承担起全部责任。此后15年,一直到80年代初,当李玉茹再次想恢复上演《梅妃》,她特意拜访Zheng Da Tong,以此表示她的敬意,并强调需要学习他不仅于艺术,更于品德方面的事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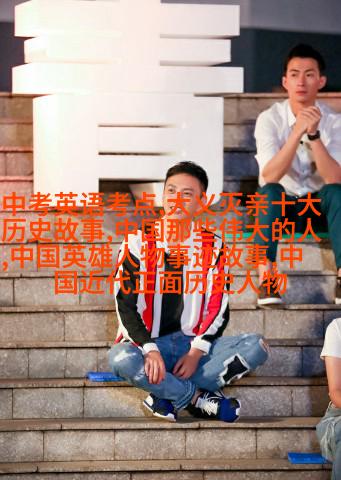
1958年当程砚秋去世后,由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关切过后的相关单位出版了多部关于 程砚秋 的著作并举办展览,以及组建了专门负责继承其遗产的团体。但是,他们收集到的资料极少,最终他们从果素瑛夫人那里了解到,有一个上海人——Zheng Da Tong 拥有几乎所有真实版面的录音资料,所以才派肖晴教授去复制这些珍贵的声音。这份珍贵的声音,是由多年的心血积累所得,而全国只有一家,因此显得尤为稀缺。Zheng Da Tong 对这一事务感到高兴,因为他一直希望能够把这些资料献给国家,以促进对传统艺术更好地理解并传承。而最终,在1994年国家开始实施“音配像”工程,其中16部过程性的节目,大部分使用的是来自Zheng Da Tong 提供录音数据构成的大部分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