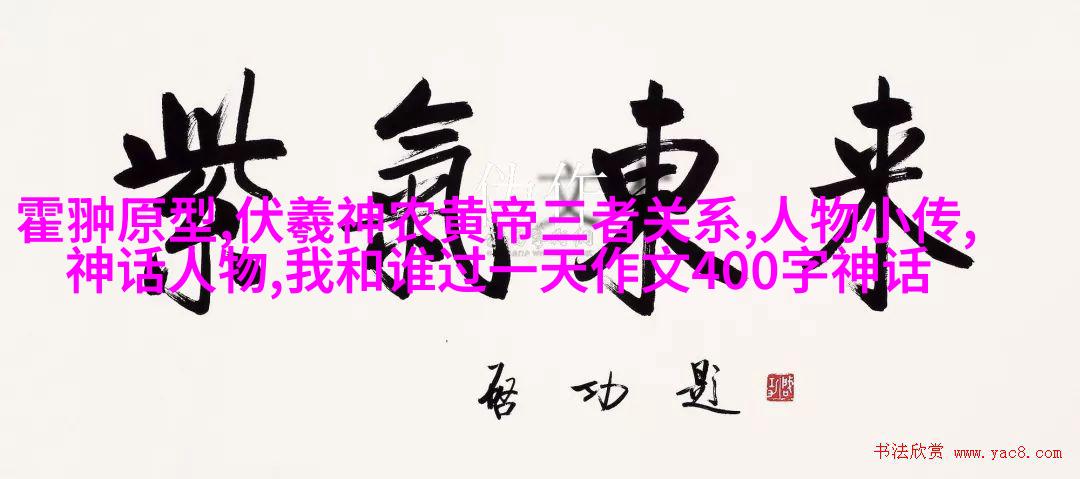在湘西家乡的儿时,刘海军梦想着大海。成长后,他来到了中科院声学研究所,一年又一年地投入到水下试验中。他曾经每年平均外出试验100多天,有一次连续4个月都在海上度过。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刘海军见证了大海的辽阔,也深刻体会到了个人力量的渺小。他说:“我动手能力强,擅长做看得见、摸得着的事情。”他的这种偏好源于他从小学到高中帮家里的农活经历。

刚进所不久,刘海军就被派往湖北宜昌出差。水声系统中的相控发射阵出现了问题,他们需要就地进行试验设计。为了节省时间,他和同事们吃住在水库旁边的废弃工厂里,“大家都想早点解决问题,就没日没夜地干”。他们发现可能的问题,要将设备挨个拆改焊接,再入水验证。当时经费有限,没有辅助布放的工人和吊放装置,每次试验都要拉着设备出入10多米深的水中。
去的时候还是炎热的夏天,完成试验时已经是冬天。“大家这才觉得冻得难受,不断感慨‘好冷、好冷’,一刻也不想待下去了。” 刘海军回忆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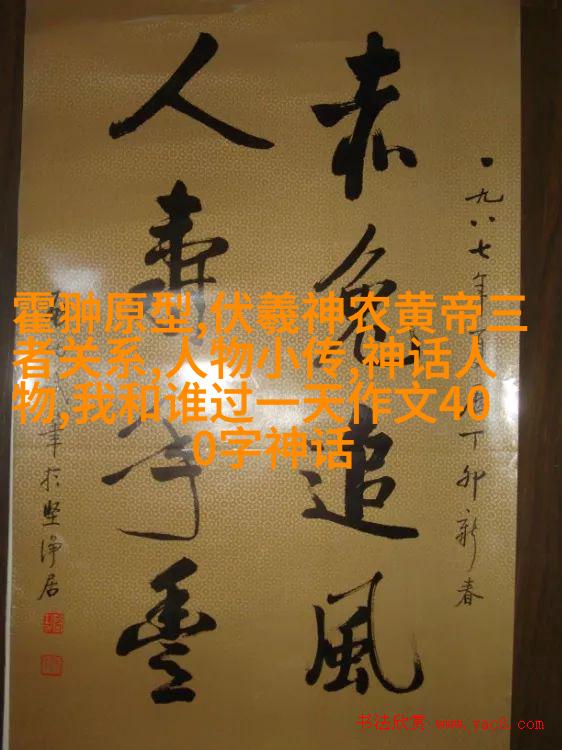
作为利用声波这把手术刀“解剖” 海洋的人,刘海军面临的是设计和拆改设备以及应对突发事件等难题。无常的风浪、突发的事故,都可能带来致命后果。
2016年南海的一次试验中,当船行至文昌附近恰逢台风经过。当时天很快变得乌黑,一连串的大浪和漩涡把船抛起扔下。“我们像是坐在一辆高速行进的汽车里,上面铺满了宽而高减速带。”

此后一个多月,从不晕车的小伙子晕车反应变得十分强烈,这似乎唤起了身体早先记忆中的痛苦。而那次宜昌山区水库试验给他留下的“戳”,就是左眼眼白处始终有一个红点。一旦熬夜用眼,那红点就会凸出眼睛布满血丝,看东西模糊。这都是因为焊锡蹦进左眼造成烫伤之后未能及时处理导致。
尽管如此,在18年的工作生活中,只要困难摆在前面,他只想着怎么解决它,就像种田一样,一陇一陇劳作总会耕种完。一旦解决掉,就非常有成就感。他告诉《中国科学报》,带着使命和责任去工作,就觉得这些苦难都不算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