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片宁静的自然风光中,郑大同深陷于京剧史论的研究之中,他不仅是一名学者,更是位热情的票友。每当他演出《贺后骂殿》的那一幕,“有贺后在金殿一声高骂”,台下掌声雷动,他仿佛被这艺术世界所吸引,几乎忘却了世间的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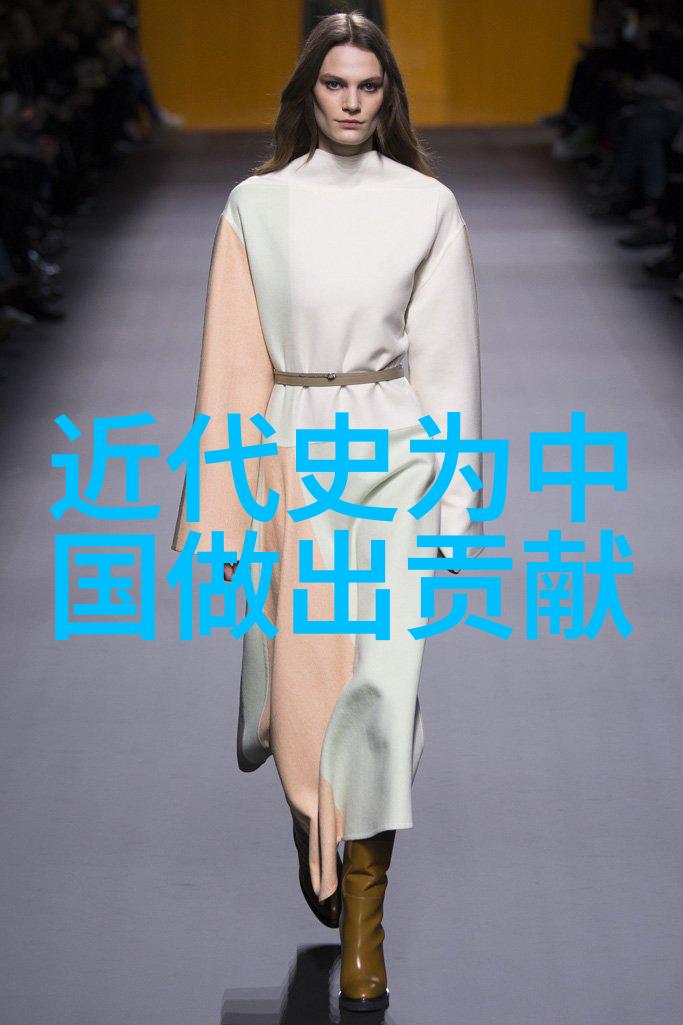
随着时间的流逝,郑大同成为了程先生忠实的追随者。在上大学时,他常常带着冷烧饼去看程先生表演,每次散场后,都不得不爬墙头回校。他对程派艺术的热爱和敬仰,让他放弃了蜜月旅行,而选择跟随程先生到上海。
1942年,当郑大同刚从美国哈佛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回到天津时,他与新娘子一起天天去戏院观看程先生表演。他的热心和忠诚没有逃过程先生的眼睛,当他们第一次见面时,程先生感动得要命,并成为至交密友。每次相聚,他们会聊到深夜,互相学习,一起探讨京剧艺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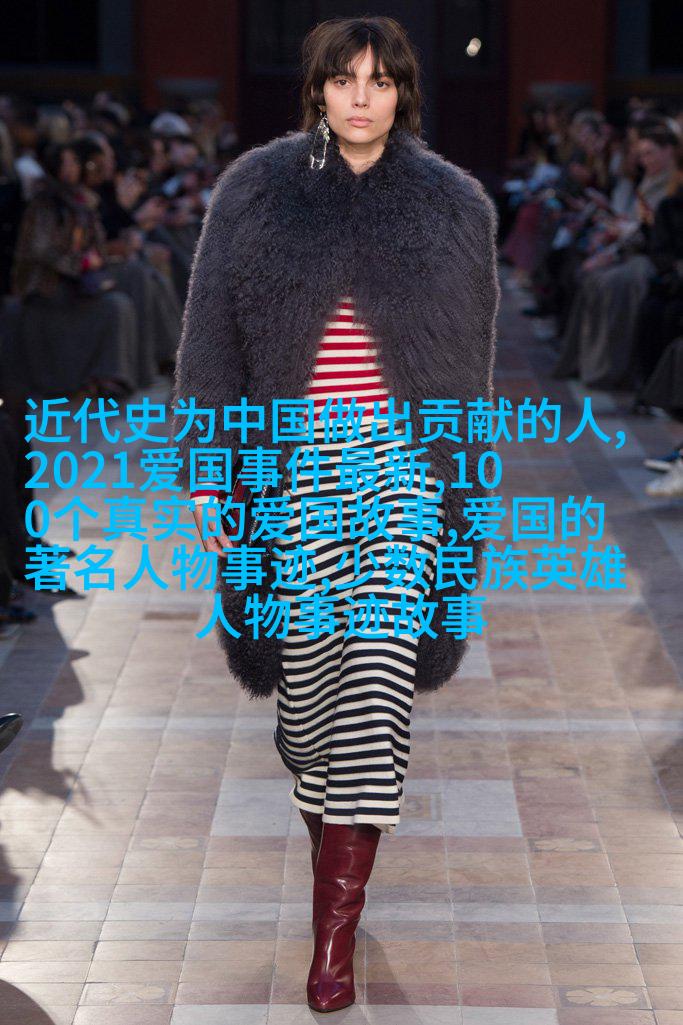
1945年钢丝录音机问世,价格昂贵,但郑老师并未放弃。他四处筹款买了一台,用来收录程先生实况演出的珍贵声音。在那个充满喜悦的心情下,1946年9月,在上海连续进行36场传统戏曲演出。这些珍贵的声音成了郑老师宝藏,也是研究京剧历史和艺术的人们不可或缺的情报来源之一。
1963年8月,当江苏省青年京剧团在上海举行演出时,公安局长黄赤波向钟荣介绍了郑大同老师。当钟荣在短短四个月内学会了五部戏曲中的全部唱念,这一切都让郑老师感到无比激动和自豪。他的教诲如同灯塔一样,为那些渴望学习京剧的人指明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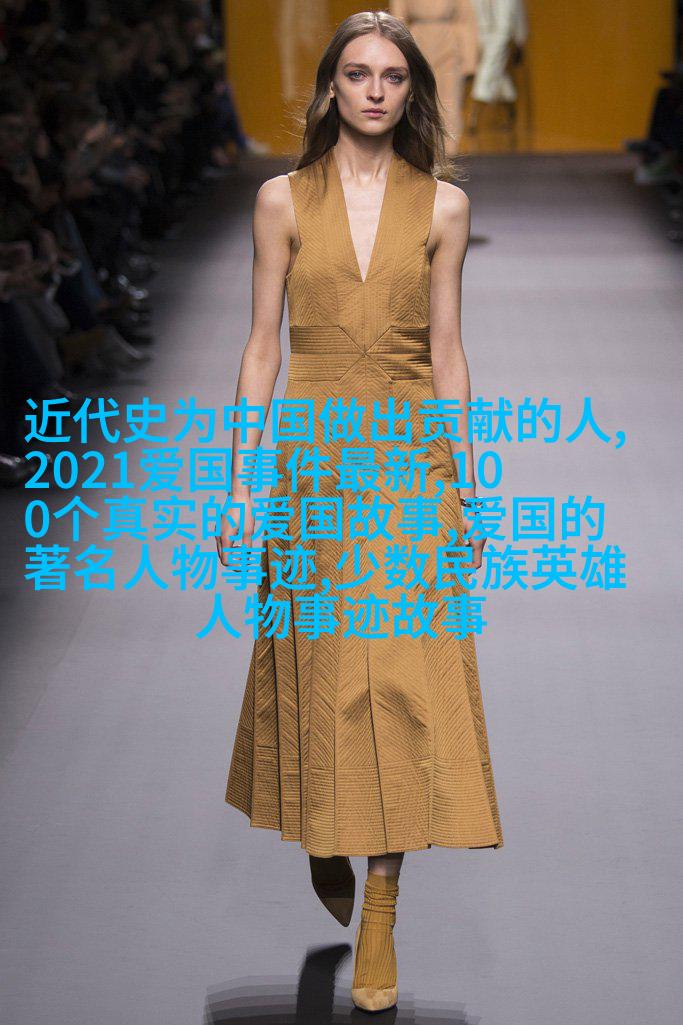
1953年的26场《祝英台抗婚》让他与夫人共同记录下来,将整套完整剧本作为礼物赠予钟荣。这份厚重而又精细的手稿,不仅反映了程序上的变化,更体现出了一个不断进步、不断完善的艺术家精神。而且,即便是在政治风浪中,对待朋友依旧保持真诚,与人为善,是他最为人称道的地方之一。
20世纪60年代初,当李玉茹上演《梅妃》轰动上海滩的时候,没有人想到,那将成为十多年后的复古罪证。当李玉茹因此被批斗,而郑大同时陪斗,这种事件才真正暴露出了文化运动中的荒谬性。但即使如此,无怨无悔地承担责任,是他坚持不懈的人品所展现出来的一面。在80年代初,再次恢复《梅妃》,曹禺夫妇也曾求教于他,以此来彰显文艺春天时代价值观的大变迁,同时强调学习他的艺术也是必不可少的一环。

1958年当周恩来总理关注并推崇京剧继承发展后,不断出版各种关于程砚秋作品及资料,并设立专门展览。此外,还抽调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政委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到北京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首都卫戍区文化娱乐部门”,以确保这种文化遗产不会消失。在周总理支持下,由中国戏曲学院音乐家肖晴前往复制所有珍贵录音资料,使其能对未来节目提供帮助。此事还涉及到了国家“音配像”工程,从1994年的16部过程中绝大部分使用了这些材料,因此可以说这是非常重要且具有里头故事的一个元素。一生致力于保护和传播这门美丽舞蹈语言的是我们今天正在讲述的人物——正是这个名字响亮、影响深远的事业伙伴——郑大同。
